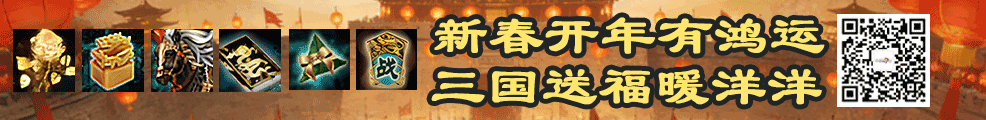|
(0)汜水的交臂 世上有很多种不明智,比如不辨天时,不识时务,不列陈力……归根到底说就是一种愚蠢。愚蠢是可悲的,但是一往直前的愚蠢,我们不妨送他六个字“自作孽不可活”。
封建时代的贵族身份是很令人仰视的,当然,现代也一样,所谓的官宦子弟走路的姿势在平常小民的眼睛里都那么不一样,从权乎?崇权乎?其实都差不多……非要用个词把这种感觉概括的话,那只有“敬畏”这个词了。“敬”代表崇权,“畏”代表从权。对待比自己身份地位高的警卫一些不是坏事,进可以通达,退可以自保,何乐而不为?但是,以高官自居者3,也要小心,你狂可以,但不能狂得太投入,成了惯性,狂错了地方,对于未来也是个麻烦了……
袁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是因为次人什么都敢做,果敢得不得了。袁术的身份确实也算高贵,背着四世三公的社背景,在那个封建等级分明的时代,不自骄也难。在十八路诸侯联军的时候,袁术也作为一镇诸侯加盟。对于这次联盟,袁术无疑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不能怪他,因为那个时代,以他的身份加入盟军,对于其他诸侯是一种鼓舞,因为董卓乱政,同盟军需要背景比较深的人加盟,无可厚非,为了突出自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袁绍和袁术的加盟,无疑使盟军的档次上升了一截子!而袁绍年长于袁术,所以做了盟主,而袁术却不是很服气,因为这涉及家事,袁绍虽长,但是是庶出,袁术虽年逊,却是嫡出的。在嫡庶分判的封建时代,这个优越感不是一点半点的。我们先来看看《演义》中的一段描写: 袁绍曰:“绍虽不才,既承公等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众皆曰惟命是听。绍曰:“吾弟袁术总督粮草,应付诸营,无使有缺。更须一人为先锋,直抵汜水关挑战。余各据险要,以为接应。”
这段文字体现的袁绍的心态,他很在乎袁术,这种在乎的感觉很微妙,总督粮草是重任,袁绍第一件是就是给袁术安排这么重要的职务,肯仪看出,袁绍尽量想让袁术的心理平衡些,所谓“总督”,就是全部负责的意思!这样的任务需要的能力可想而知,但是袁术根本没有商榷,就直接下达了指令,是因为他不能商榷,自己的身份已经是盟主了,袁术如果仅仅作为其他的十七分之一的面目出现,袁术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索性给他个要职,这样袁术就不会弄出什么事来了。可见袁绍的处世方法很“小”,这样的安排无奈也好,面子也罢,却给盟军的前途铸成了大祸。
由于孙坚屡战屡胜,袁术有犯了老毛病,怕孙坚抢了风头,竟然不发粮草!大家不妨注意这个细节,袁术由于一己之私制造的这个事件是第一桩认为破坏联盟军战斗力的事件!这样的过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大家人人都明白,而对于孙坚,袁绍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是〈演义〉中的一段描写: 坚为折了祖茂,伤感不已,星夜遣人报知袁绍。绍大惊曰:“不想孙文台败于华雄之手!”便聚众诸侯商议。众人都到,只有公孙瓒后至,绍请入帐列坐。绍曰:“前日鲍将军之弟不遵调遣,擅自进兵,杀身丧命,折了许多军士;今者孙文台又败于华雄:挫动锐气,为之奈何?” 这段描写将得很清楚了,袁绍是盟主,以孙坚的为人,既然是共图大事,首先,他不会太向袁绍发难,有道是“疏不间亲”,这个时候自己吃了败仗,在报告中大骂盟主的兄弟,一来是仗已经败了,骂死了又有什么用?二来,骂了也作用不大,袁绍还能把袁术宰了不成?(平心而论,袁术的罪足够处斩的)三来,毕竟是孙坚被华雄劫寨致败,要负些责任,这个时候退位罪责,对于孙坚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总有些没面子。所以对于袁术的事件,孙坚没有把事情闹大,〈演义〉中袁绍的那个“大惊”被罗贯中用得很传神!袁绍对孙坚的败完全出乎意料。试想袁绍如果知道袁术不发粮草,对于孙坚的失败,袁绍纵然不责备袁术,也不会大惊的!那个时代谁没打过仗啊?谁都知道粮草缺乏对于战事的危险性!所以这样的失败是能够合理解释的,不需要“大惊”。纵然孙坚的呈文中有提及,估计也是一笔带过。孙坚也不傻,仕途时代嘛,惹了他四世三公的人,官还当不当了?!英雄不怕为国捐躯,就怕报国无门。你孙坚好容易进了门一般委屈能受就受。一场仗,为了国家,反正也败了,犯不上时候再说谁谁谁负主要责任。袁绍呢?同样也很明智,你孙坚一笔带过,我就同以一笔淡之。当中责备自己的弟弟有失面皮,脸上也不好看,毕竟是一家子,所以开总结会的时候,对袁术之字没提,反而把死鬼鲍信和倒霉的孙坚拉来疏落了一番(反正一个在黄泉,一个在前方,都听不到……)袁术呢?这样的包庇不但没让他收敛,反而更加不知好歹了……
众将被华雄难倒在了汜水关,一筹莫展的时候,关老爷站了出来,乞斩华雄!这时候袁术的举动更加疯狂,看看演义中寥寥几字但出乎其神的描写吧: 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 袁术不但无缘无故的发出“大喝”这样高分贝的声响,竟然还以区区一个同盟议员的身份主观作出“打出”这样的仲裁。读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袁术“凭什么”。你袁术不是盟主,其他诸侯手下的人,怎么能想打就打,想轰就轰?公孙瓒的面子往那里摆?而且这样做给袁绍一点儿脸也没留!很明显,袁术狂傲得根本没有把十六镇诸侯放在眼里,包括袁绍。因为他自认为家庭地位压倒袁绍,社会地位压倒群雄,根本是肆无忌惮,纵然不是盟主,也根本没有人可以顶撞他。而且当时的袁术狂到了近乎“疯”的地步,〈演义〉的描写如下:
绍举目遍视,见公孙瓒背后立着三人,容貌异常,都在那里冷笑。绍问曰:“公孙太守背后何人?”瓒呼玄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刘备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黄巾刘玄德乎?”瓒曰:“然。”即令刘玄德拜见。瓒将玄德功劳,并其出身,细说一遍。绍曰:“既是汉室宗派,取坐来。”命坐。备逊谢。绍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于末位,关、张叉手侍立于后。
可见一斑,“瓒将玄德功劳,并其出身,细说一遍”功劳不算,谁没打过几场胜仗啊?不新鲜了。关键是出身,刘备是汉室宗亲,中国有句老化叫“瘦死骆驼比马大”,论根红苗正,刘备的身份比你四世三公硬多了!袁术呢?还瞧不起!为什么?嫌人家刘县令官小……袁术就是这样一个自恋者,从谁身上都能挑出毛病,找出不如自己的地方,转而成为自己耀武扬威的资本。要不他手下没人才,因为人才都聪明,看穿了这个,谁还跟他啊?(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也不叫人才了)
温酒一盏,擂鼓三通,华雄的首级已经被关羽抛到了营前!“众皆失惊”的时候张飞的一句话非常合理---“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华雄被杀,敌军无首,着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战争是讲一鼓作气的,如果袁绍果断,拿下汜水不会有太大问题。偏偏这时候,袁术又起来了!而且,对于其语言的描写把袁术的形象搞得很可笑和滑稽: 袁术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曹操曰:“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袁术曰:“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 “尚自谦让”,听着啼笑皆非,战争是生死的较量,就听说“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身先士卒,当仁不让”的,鲜有对战争运筹,临阵却敌要谦让的。袁术的情绪已经失控,也许是目空一切的习惯使然,他看不起身份低微的张飞,毕竟张飞没有立功,凭什么在这里猖狂,但后面那句“都与赶出帐去”,也就是说,连关羽都要赶!要知道当时的情形,华雄杀得几路诸侯傻了眼,关羽出马,解了多少诸侯计穷之困?又减少了多少我军的损失?关羽在诸侯心里的形象不言而喻,但是袁术这时候竟然能逆流而上!大骂战场功臣(也可以说是大骂国家的功臣),可见其目空一切之甚!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武大郎开店”似的嫉妒。而这个时候,作为盟主的袁绍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还是曹操及时解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颇有道理,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无可厚非的。理亏的袁术又开始转移话题:“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面对以大家为重的曹操,袁术的布置好歹无异于撒泼,在他心里,这些人都不配和自己共语,可万万没想到一下子出来这么多跟自己过不去的!我袁术四世三公的出身,你们竟然不服我,帮个弓手和县令?!我用走吓唬你们!而曹操此时也不愿意得罪盟主的弟弟,更多的是从大局出发,那句“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使人物性格尽显,委屈了桃园兄弟,但整个盟军的“皆散”却完全错失了一次占得先手的大好机会!
纵观〈演义〉全篇,袁术在这个时候是罗贯中使用语言刻画手法最多的,甚至是在“温酒斩华雄”这个故事中,花费笔墨刻画最重的!由于语言的冲突性使文学艺术形象尽显。袁术的轻慢和狂妄跃然纸上!当然,他的狂妄是有资本的,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在那个时代可以使他慢待任何一个人,因为过惯了官场生涯的他深谙“崇权和从权”的风气。 一、荥阳的箴言 两军交战就是拼命拼策加斗运气,运气好的九死能得一生,运气不好的连神奇都能化为腐朽。对于败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回忆战斗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然后对自己轻声地说一声“很幸运,我活了下来”……
三国时的战争就是这样,那一方都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并不是处于一种自我安慰。是因为那个时代对于“忠义”二字的重视。连董卓这样的人都要打着仿效伊尹,霍光这样的旗号来聚众讨论废立,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怕人说出闲话;连没有什么目标只知道当皇帝比做四世三公舒服的袁术都要去攀扯“代汉者当涂高也”来让自己和别人觉得自己很合适皇帝的职位。一有大的举动,或发动战争,为公也好,为私也好,各种各样的人总要把自己跟忠孝节义挂上钩……无论如何都要肯定,那个时代的人比如今的人要脸的多……
由于董卓乱政,十八个根本不该联合的军团联合在了一起。开始研究一种叫做“同仇敌忾”的行为,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对董卓的讨伐行动。其实在汉末这种皇上罩不住的政治局面下,所谓的精忠报国都是有不少的水分的。人性是不是本恶的本人不敢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句话在那些太守,刺史之类的英雄们心中都会念叨几遍,这种现象很正常——讨董卓就是因为董卓失德嘛。要不然这些诸侯也不会忙不迭地加入这个队伍,急于和“有德者”产生关系。而对于皇帝来说,这样的战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用十八鬣狗去咬死一头豹子,皇帝真正享受的不是平安,而是享受这只曾经给自己带来痛苦的豹子死亡时自己得到的快感罢了。
十八镇诸侯有几个确实卖力气,也有几个墙头草,更有几个是消极怠工。要说卖力气的,恐怕不外乎孙坚和曹操了。孙坚此文不表,单说曹操——发起者是他,选定盟主的是他。可见曹操对于除去董卓可算真的用了心,当初敢斗胆去孤身行刺董卓就可以看出他不仅胆子大,而且真的是为了正义而正义,行刺这中行动几乎是必死的,可不比一般人唱句国歌那样简单。而且曹操很爱国,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可以以死相报,不然当时他也不会选择和董卓同归于尽了。由来联军成立后,他更是毫无私心,大胆任用关羽,并常常在袁绍面前献策。虎牢关一战逼得董卓迁都长安。此时众诸侯见赶跑了董卓,就立刻拿出了小富即安的少爷作风,只有曹操如坐针毡。显然曹操此时的举动已经明显有别于其他盟主了,而且在一片反对声中,敢骂出“竖子不足与谋”这样伤众的话来,更是显示了曹操对于联盟的失望!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地运筹,盘算,为了国家利益这般用命,竟然找来了一群废物!开始还想集结兵力,哪成想连这么基本的要求都成了奢侈。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自己带着数万人马来赶董卓……
在荥阳城外,曹操中了李孺的计,让两个兵卒戳倒了战马被擒。这时曹操的心理也许是一片空白,他很委屈,甚至是一种受侮辱的感觉。不是因为自己被擒将会直面死亡——他可以说在决定行刺董卓的那一刻,就为自己诠释过死亡的定义。他委屈的是自己费尽了心机成画饼,好比一个付出了全部感情的人被感情抛弃一样。面对着一盘散沙的爱国统一战线,想着这一场场不尽己力的战争,再往前追溯一下把马血涂在脸上,张着大嘴高喊“我爱祖国”之类口号那一张张丑恶的嘴脸!曹操也许真的觉得死是世界上最过瘾的事了。此时的曹操真的开始痛恨那些割据势力,说真的,他们不配。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对于自己带来创伤的事物,自己就要他们也没有好果子吃。曹操在诛杀董承之前,真的算一个相对完美的好同志,甚至可以说,他所做的事情大都是为了国家着想的。真不敢想象曹操如果此时被杀,天下会成为什么样子!此时的天下地方割据势力很多,在曹操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前的那段时光里,汉室江山几乎是一个不能定性的时代——有打砸抢的(董卓),有挟持国家元首和国家干部的(李郭),有私藏国宝的(孙坚),有为了抢地盘找人码架的(袁绍)!不看人物,就这几种社会现象怎么看怎么像香港电影中屡见不鲜的三十年代上海滩。在这种社会,曹操不管是处于什么目的,能够站出来做出这种于当时风气格格不入的举动已经不啻为一种革命了。尽管他也知道是驱虎吞狼但是没有办法。也许自己想过会失败,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组织这种活动竟然要面临被活活气死的命运!
多亏了曹洪救驾,曹操得了一条生路。在以后的时间里,曹操边挟天子征剿四方,边自己培养自己的队伍,不再轻易跟谁联合了,《演义》中也鲜有曹操主动去和某某联合共同讨伐一方的现象。一来是曹操有天子的名号罩着,干什么都是一种“合法”,二来是自己的势力非昔日可比;这第三,打不过对手可以晚两年打,别再跟谁联合了,十八镇诸侯这事够曹操记挂一辈子的,不仅仅是死里逃生,还有在荥阳得到的那个无语的箴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7 16:21:45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