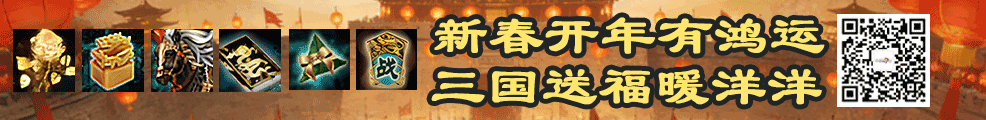|
五、 走麦城
孙权在给曹操写信的同时,秘密带军东进,以吕蒙为先锋。吕蒙把部队秘密地集结于寻阳,从那里隐蔽地登上“鞲轆”。鞲轆是一种船的名称,但这种船的式样今天已不可知。从该词的造字结构,并联系上下文看,鞲轆应是一种大型的皮筏;由于是皮制,故没有任何战斗力,只用于长江沿岸的商务运输。吕蒙以这一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船运送兵力,并“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以期最大限度地隐蔽意图。他“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侯(警戒哨所)”,关羽沿途所设的哨卡都对这些船没有防备,来不及发出任何警报就被一网打尽,“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公安守将傅士仁、留守江陵的南郡太守麋芳经过一番犹豫后,都投降了。吕蒙不战而占领南郡。
傅士仁、麋芳之所以轻易投降,除了吕蒙以优势兵力突然出现,给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之外,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素嫌羽轻己”。关羽这次出军,麋芳、傅士仁负责后勤供给,很不得力。关羽气愤地说:“回去再和你们算帐!”“芳、仁咸怀惧不安”。还有记载说,麋芳早就与孙权眉来眼去。
吕蒙进城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吕蒙的一个同乡“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下令把他斩了。
在吕蒙占领南郡的同时,陆逊率军攻略南郡周围各城,连下宜都、房陵(今湖北房县,为新城郡治)、南乡诸郡(新城、南乡均为曹操所置郡,按理说不应在攻略的范围内,故而《三国志·吴主传》只记载了“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而没有攻略新城、南乡的记录。可能是陆逊曾击破了这些郡县——当时可能落入关羽手中,也可能是一种误会,但不久就归还给曹操),屯兵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切断了荆、益两州的联系。这样,孙权利用伪装、诱降、收买人心等多种政治、军事手段,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荆州南郡。
关羽率军返回时,由于官兵的家属都在吕蒙手里,军心不定。而吕蒙也积极作关羽兵将家属的工作,“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由于孙权与刘备还有结盟的关系,关羽在返回的路上,不断派人给吕蒙送信,希望用政治手段解决争端;吕蒙乘机用计,“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关羽的信使返回后,关羽手下“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大批士兵逃回荆州,仅孙皎一部就收容关羽逃兵五千人。不久,孙权率领主力也赶到了。关羽见势单力孤,只好退往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
这时,刘备的义子副军中郎将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刚刚率兵占领了上庸。关羽在包围襄、樊时,就多次派人“令发兵自助”。但刘、孟二人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加以拒绝。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败退的关羽及其子关平、都督赵累在麦城郊外章乡被潘璋的司马马忠俘获,随后被杀。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往洛阳,交给曹操,而用诸侯的礼节下葬了关羽的躯体。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把几年前俘获的原皖城太守朱光送还,“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曹操、孙权之间的关系迅速热乎起来。
襄、樊保卫战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性。曹操连续派兵加强荆州,在七月已经取得了对关羽的优势。不料,一场罕见的大雨引起了汉水泛滥,曹操派往荆州的主力被洪水吞没,丧失殆尽,仅余樊城一座孤城在洪水中飘摇。
意外的胜利似乎冲昏了关羽的头脑。他想乘胜攻克襄、樊,充分利用这一胜利。不想在樊城坚城之下受到重挫,不仅樊城未能拿下,自己的主力也被援军徐晃击败。更为可怕的是,孙权黄雀在后,乘虚袭夺了荆州,关羽上演了一出“走麦城”的悲剧,兵败身亡。
作为一个独立战略区的最高首脑,必须随时对自己的战略任务有清醒的认识。关羽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在曹操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保卫住荆州,而不是从荆州出击,这是全部问题的前提。从这一前提出发,当关羽在老天爷的协助下一举全歼了曹军主力三万人后,特别是在襄阳守军投降后,理应见好就收,以必要兵力守御襄阳,改善自己的防御态势,主力迅即回防。区区樊城一座孤城的得失,对荆州的安危无关痛痒,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至于曹操一直担心的樊城失守后,关羽会乘虚直捣许县,则根本不应在关羽的思考范围之内。他的任务既明确又艰巨,那就是必须在曹操、孙权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能顺利地保住荆州属于自己的两个半郡。
关羽在樊城前线作战时并非没有顾忌到孙权可能的偷袭,他在公安和江陵都留下了重兵,还在江边留下了观察哨。他认为,只要这些观察哨观察到孙权的军事调动,公安、江陵能防守几天,他就能从前线退下来,投入对孙权的作战。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些措施在真刀真枪的军事对抗时能够发挥作用,但在阴谋面前却可能不堪一击。
关羽行武出身,他所推崇的就是武功赫赫,一味地崇尚武功,使他最终在阴谋面前败下阵来。
关羽个人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一个原因。据史书记载,“(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吴军一举,公安(时为荆州州治所在)守将傅士仁、南郡(为荆州在刘备手中最重要的郡)太守麋芳先后投降。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坚守十天左右,关羽就可以赶到,历史可能重写。
后世一再指责孙权乘虚夺取荆州的举动是不顾大局,贪图小利的短视行为。我认为这种指责有失偏颇。作为一个独立政治集团的领袖,孙权显然不能把事关自己生死存亡的大权交在别人手里。占领荆州剩下的几个郡,则北可以据江、汉而对抗曹操,西可以借三峡而封闭刘备,依托长江便利的运输,可以快速机动兵力,把战略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是比依靠刘备的善意,对孙权更有利吗?还可以问一句,如果刘备终于发展起来了,要迈出统一中国的步伐,他是会为了同盟的利益而先攻击曹操呢,还是会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而先打击孙权呢?恐怕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其实,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在各自的战略设计中,同盟的另一方都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战略威胁而不是战略利益来加以考虑的。建安二十年,两家的矛盾一度发展到战争的边缘,仅仅是由于刘备担心更重要的战略利益——益州受到损失,作了单方面的让步,才暂时缓和了这一矛盾。此后,孙权在陆口、在夏口,都是委派最得力的官员,配属以重兵加以镇守,对荆州的顾忌和觊觎一目了然。
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还可以看到,十多年来,孙权的战略行动是前后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夺取荆州,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流域。开始与黄祖、刘表争战,目标是荆州;曹操占领荆州后与曹操争战,目标也是荆州;刘备占据荆州后把矛头指向刘备,目标还是荆州。他为了荆州而与刘备结盟,又为了荆州与刘备反目,战略思想是很连贯的。
曹操在襄、樊保卫战中的得失有些难于判断。就曹操的本意,他总还是希望孙、刘两大集团能“缓则相图”,在建安二十年,他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战略,原因是关羽的威胁实在是太强大了,大到无法接受的程度。从曹操的军事部署看,曹操并不希望与关羽决战,而只是希望在边界上多少削弱一点关羽的力量,打击一下他的政治威望,但又能使他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孙权。但人算不如天算,一场洪水吞没了曹操派往荆州的大部分兵力,而南方的战略支撑点樊城也岌岌可危。曹操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来堵塞这一漏洞。即使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曹操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战略利益所在,它不在于彻底击溃或歼灭关羽,而在于引关羽东向对付孙权。但甚至在他主动地把孙权即将偷袭荆州的消息近乎背信弃义地传递给关羽后,关羽还是执迷不悟。关羽一口咬住了樊城,就象狗咬住了一块骨头,说什么也不松口,逼得曹操不得不把他击溃,才能解脱出来。
在关羽被击溃后,曹操还命令得胜之师不许追击,以“多权之敌”。但由于孙权的计谋实施得太成功了,而关羽又是如此天真,以致未经一战即全军瓦解,曹操的图谋未能实现。武功盖世的关羽最终被证明既不是曹操、徐晃的对手,也不是孙权、吕蒙的对手。
襄、樊保卫战的副产品是刘备与孙权之间爆发于两年后的猇亭之战。在那场战争中,刘备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刘备也在不久后死去。蜀汉从此元气大伤。这一切曹操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确是他亲手造成的。
总的来说,襄樊之战,曹操达成了削弱来自荆州敌对势力的政治影响的任务,稳定了自己的战线,尽管代价显得大了些。
孙权借曹、刘相争的机会,以极小的损失占领了他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荆州,获利最大。只有刘备是一个大输家。他先是损失了关羽这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和荆州这一重要的战略出口,后来又在猇亭之战中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精锐军队,战略势态严重恶化。
|